【浮光弄色】(20)作者:洛笙辭
2025年3月31日發表於pixiv===============第二十章:虚实相生·危中埋伏“阁主,请留步。”秦淮脚步未停,眼角微挑,唇边浮出一丝笑意。那笑不温不火,如深夜窗纸后的灯影,看着明亮,却无法窥透其后。“景公子。”他声音温润如玉,语调却仿佛藏着一柄细长的钩刀,“果然是在等我。”他身后并无随从护卫,唯有两个年约十二三的小童子,一个抱琴,一个提壶,衣袍整洁,脚步轻盈,看着竟像是随秦淮游山玩水来的闲童。他向前踏了一步,拂袖而入,未曾多言半句,竟有种主宾倒置的从容。我转身,让开身位:“阁主既至,便请入座。”浮影斋内灯火通明,朱红窗棂边垂着竹帘,四方食客笑语喧哗,酒香混着烤鸭香味穿过两道回廊,弥漫在夜色与灯火之间。“今夜好热闹。”秦淮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厅堂,忽而一笑,“这东都近来荒芜了不少,倒不如景公子的斋馆热气腾腾。”我微笑:“民以食为天,浮影斋也不过仗着旧街口的地利,承些旧客罢了。”但他不知,或是不点破——浮影斋此刻看似热闹,实则每一席、每一客,皆是我布下的一道棋。屏风之后,一位“酒客”醉眼迷离,却手握藏刃,轻轻转动指节;楼上雅阁内,一名“说书人”懒懒支颐,其实是柳夭夭亲自伪扮,她的眼神透过竹帘缝隙,时刻不离秦淮衣袍翻动的每一寸;而屋脊之上,一道人影蹲伏在角檐之处,犹如猫伏鼠行,正是陆青。他整个人几乎与屋瓦融为一体,只一双眼眸清冷如夜,死死锁住那两个看似天真的童子。杀局已成,风却未动。我引秦淮入主位,他拈起茶盏,轻轻抿了一口,忽而似笑非笑地道:“浮影斋果真雅致,不说这茶香,只这陈设,也胜过瑶香阁七分。”我不语,只微微颔首。他放下茶盏,眸中似有玩味:“只是——少了些柔情。”我眉梢微挑。他便笑了起来:“听闻景公子身边红颜环绕,沈氏小姐、林家姑娘、还有那位……柳姑娘?”我笑而不答,只顺势斟酒:“阁主消息灵通,小楼旧事也能知晓,不知是耳聪,还是眼明?”秦淮抚掌:“是人多嘴杂。何况,‘浮影’之名,近来可是传遍东都。”“不过,”他顿了顿,目光落在我面上,“今日却未见诸位夫人作陪,倒是令人失望。”我仍不接话,只道:“他们偶有私事,今晚不便相陪,阁主见谅。”秦淮不再多言,慢慢靠入椅背,一手搭于扶手之上,似不经意地敲了敲:“景公子,你邀我来,不会只是为了一壶春酿罢?”终于切入正题。我眼中微光一闪,轻声道:“阁主快人快语,那我也便不再拐弯抹角。”“是为了‘密函’。”我缓缓吐出两个字。秦淮敛了笑,低头端起茶盏,盏沿在指节间缓缓转动,却不饮,只轻声回了一句:“哦?”那声音极轻,却仿佛夜雨入地,无声之中,已润过心骨。秦淮指腹缓缓抚着茶盏,微垂眼帘,语气温柔,却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钩意:“景公子这几日,可是动得颇勤。”我垂眸为他续了一盏,淡淡一笑:“东都地大人多,初来乍到,总要走动几遭,熟悉熟悉旧街。”他抬眼看我,眼神中不带火气,偏偏令人如芒在背。“熟旧街?这倒是说得巧。”他笑着捻起桌上香瓜子,指尖轻轻一弹,声音脆响,“你从醉仙楼走了一遭靖庙废坊,转回来又去了旧书巷,第三日还请了夜巡司的朱晏喝了半日花雕……若不是我知你是大夫,倒要怀疑你是来打探东都水脉的。”我眼神未变,唇角笑意不减,只将茶杯往他面前推了推:“也许归雁镇的老友知道我来东都,特地托人来找我小聚几回,叙旧聊旧事,倒不如秦阁主这等人物,自有美人好酒,不必沾这世俗烦扰。”他顿了一下,缓缓道:“这位故人……也是为‘密函’而来?”我扬眉:“阁主不是一直说,东都谁人不觊觎密函?”“那景公子呢?”他问得更直,“是觊觎者,还是持有者?”我一怔,抿了一口酒,随即轻笑:“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。阁主布子东都多年,夜巡司虽恨你,朝堂却容你,密函落你手上,才是合理之举。”秦淮眸色深了几分,身后那两个童子静默如钟,几乎连呼吸都听不见。他低头嗅了嗅杯中酒香,忽而叹道:“这酒太烈。”“怕是容易醉人。”我顺着他的话接下去。他抬头看我,笑意再次浮现:“你总这样,话里话外虚虚实实,让人听不出几分真假。”“那就看听的人,是想听真,还是想听假了。”我们目光相交,四下热闹如常,可心中已杀机暗涌。秦淮不再试探,而是慢慢道:“有人说你已得密函,有人说你得了一张假的,还有人说——”他顿了顿,语气忽而轻柔如絮,“你其实并不知道那密函,是真是假。”我不答,捻杯盏,用指腹摩挲着杯沿:“真假,在未揭开之前,都有其用处。就如这盏酒,入口之前,你永远不会知道它是醉人的烈,还是醒脑的清。”“那你便信你手里的……是真的?”我垂眸:“我信它有价值。”秦淮静静看我良久,终于轻笑一声:“这三天你布了一局,可我仍看不清结局。”“那就别急着看。”我对他轻轻一笑,声音淡淡,“等你看清的时候,或许已经在其中了。”他没再说话,举杯饮尽。那一杯酒下肚,已然入了局中。我将酒盏放回几案,指尖轻敲桌面,语气忽然一缓,不似先前的凌厉试探,倒像是真心吐露:“其实……密函之事,我本不该掺和。”秦淮眉梢微动,却没出声。我继续道:“若非沈云霁小姐托我保管一段时日,我也不想沾染这等风波。她是重情之人,曾于我有恩,我不过尽人事罢了。”他眼神稍许松动:“所以,景公子并非存心夺函,只是——一时受托?”我苦笑:“阁主也知我本是个江湖大夫,这些年来,看惯人生死已够疲惫。如今不过在东都谋个差事,图个平稳过日子……若真能从这局中全身而退,自是最好。”秦淮轻轻一笑:“这等明哲保身之言,我听了倒有几分欢喜。世人都争这密函,唯你退得干脆。”“我知道它不属于我。”我缓声道,“所以今夜请阁主来,便是想了断此事。”他一愣:“你要交给我?”我点头,不藏不掖,拂袖自怀中取出一方锦盒,呈于桌案之上。“阁主所求之物,尽在其中。是真是假,我不妄论,但我敢保,此物出自沈云霁手中,半月前便托我暂管。”锦盒通体墨底描金,暗纹隐约,封口处盖有一方沈家小印,看似尚未开启。秦淮的目光落在那方印章上,眸中深意浮动,许久未语。“你当真要将它交给我?”他声音轻得几不可闻,却隐隐透出些迟疑。我抬眸,与他目光相接:“若阁主愿收,自此你我两清。沈小姐之托,我已还情。你我之间,也再无瓜葛。”这话说得斩钉截铁,仿佛我真的从此退出纷争,再不涉足密函风波。秦淮望着我,眼中沉静似水,仿佛要从我一眼望穿心底。但我没有退,也没有掩。这一刻,我的神情中没有丝毫锋芒,唯有一种疲惫后的坦然,一种身在棋局却愿弃子出局的从容。终于,他伸手,接过锦盒。指尖触及封印的那一刻,他眼底仍有犹疑,但还是收入袖中,缓缓起身。“此事……我会亲自验证。”他语气依旧温和,“若真如你所言,景公子今后,东都自有你的一方净土。”我起身为他送行,拱手微笑:“阁主此言,景某铭感五内。”秦淮轻轻颔首,转身走出雅间。两个童子早已候在廊下,见他出来,立刻无声随行。浮影斋外夜色正浓,街灯斜照,一如初见。我目送他踏出门槛,风吹起他衣袍的下摆,恍惚间,那背影竟有几分迟疑。但我知道,真正的好戏——就在这一刻,才刚刚开始。秦淮从浮影斋大门走出,脚下刚踏上青石街砖的那一瞬,整个南街像是被抽走了最后一口气。夜色如墨,街灯未灭,喧嚣未停,但所有声音却在那一刹静若死水。连酒楼中调笑的客人,街边摊贩的吆喝,以及风中远处的猫叫声,都像是突然被人拧断了喉咙,归于死寂。他察觉到了。秦淮脚步未停,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四周。“……终于舍得出手了?”他轻蔑一笑。那一笑还未落下,街巷之中猛地破空数响!第一波进攻骤然而至。暗夜中,无形巨网如银蛇腾空,铺天盖地,带着骨裂的风声朝他头顶罩来。与此同时,地面机关被触,连环飞钉如骤雨横扫而来,交织成密不透风的箭阵。
紧接着是弥天烟雾,从两侧街口齐齐喷出,带着昏迷粉与追魂香,一刹那吞没了整条街道的光与线。秦淮神色未变,袖袍一卷,轻喝一声:“阿十,阿十一。”两名童子倏然如鬼魅跃起,一个掌风翻卷大网,劲气从指间炸开,瞬间将攻势拦腰击断,连带几根金属蛛丝当场断裂;另一个腾身而起,长袖扫开暗器,脚尖点地连翻三跃,一边口中咒念不停,一边吐出一道紫色雾光——竟将那昏迷烟粉尽数反推回去。短短三个呼吸。三波袭杀,尽数破去。秦淮仍立在原地,衣角未动,神色从容,只是指尖微屈,藏在袖中的银丝缓缓游走。“‘影杀’,手法还不错。”他缓缓抬头,望向夜色尽头:“但,够杀我么?”说罢,他身形一掠,整个人像一缕烟影,瞬间越过一座屋檐,掠出两个街区,身后只余一串残影。然而,就在他即将踏入第三个街口时,一道猩红人影蓦然从天而降!柳夭夭出手了。她换下了浮影斋中常穿的衣裙,身披夜行短甲,腰系赤绫剑,一出手便是杀招,剑影旋如怒龙,从街灯残影中甩出万道残光,直逼秦淮腰腹要害。“秦阁主——就不想听听小女子敬你一声‘留步’吗?”剑声破空,夹杂细碎机关之音,显是“影杀”为她量身定制的联动装置,若秦淮敢迎上一步,便是铺天盖地的绞杀机关从四面封来。可秦淮却仅仅侧身一转。他的脚步仿佛早已量好,恰在柳夭夭两个剑招交替之时,从剑招之隙中穿身而出,一脚踏在对面屋檐之上,整个人已远去五丈开外。“柳姑娘,”他声音悠然,“你果然还是舞得漂亮,只可惜……不够快。”柳夭夭眉心紧锁,手中宝剑猛收,眼神不善:“老狐狸果然不好缠。”夜色再沉,秦淮的身影也已融入了城中暗巷。他的方向,不是宫中,也不是瑶香阁,而是朝他在东都城西的“揽月楼”奔去——那是他的核心地盘,也是他真正信得过的防守圈。可他没有发现,正是他奔往的方向,陆青已悄悄绕路潜伏,影杀更是在他以为脱身的道路上……悄然布下一道真正的杀线。秦淮身形若电,衣袍猎猎翻飞。他脚下未停,身后柳夭夭的剑风尚未完全消散,他已掠过两个街区,直奔搅月楼所在——那是他的地盘,是东都最隐秘的心脉,也是他最后的保险。可他刚刚跃上坊前一堵矮墙,便听见一声极轻的嗤响。那声音不带丝毫杀意,亦无煞气。只像是——黑夜吐出的一个轻叹。秦淮心中猛地一凛,足下一顿,强行偏移身形,半侧身去。几乎是同时,一道寒光从黑暗中掠至——快得毫无征兆,冷得没有温度。刀从墙后出,斜斩而下,去势不疾,却藏着一种极致的狠意。陆青出刀了。他的眼神漠然,从阴影中看着秦淮腾跃的身形,像看一头被赶进笼中的老虎。没有叫喝,没有出招试探,只有那一刀,直取要害。影踏九幽。刀意极深,割裂夜色,在空中划出一道森寒弧线,宛如割裂生死之界。秦淮虽早有警觉,却仍迟了一步。他左袖猛地卷起,暗纹手套骤然撑开,隐隐有金纹浮动,将那一刀硬生生挡下。“锵!”一声闷响,火星四溅。秦淮被震得手腕微颤,气血翻涌,左臂发麻,身形后撤两步,方才稳住。他眼中寒意一闪,心知若再慢半息,陆青那一刀便会撕开他的脖颈。“……好狠。”他喉中低咕一声,面上却笑,“果然是‘寒渊’最锋的刀。”陆青未答,只一转腕,又一刀如影随形。两人瞬间斗在一起。刀光与掌风,在狭巷之间交织如网,刀每出一式,皆是封喉,掌每动一步,皆为杀命。秦淮被迫应招,虽经验老道,步步退让,却始终难以摆脱陆青那若影随行的贴身压迫。十数个回合。街石碎裂、砖屑飞扬,秦淮脚步沉重,心头已是微乱。陆青的攻势如毒蛇缠身,不给他任何喘息之机。这时,柳夭夭赶到。“原来你躲在这儿。”她声音清脆,剑已出鞘,带着她独有的那种灵动与轻盈,如风中桃花,娇艳却藏针。剑尖一挑,直击秦淮肩胛。秦淮怒喝一声,双掌猛推,将陆青逼开半步,偏头避剑,却也因此让出破绽,被柳夭夭划破衣襟,血珠乍现。陆青眼中寒光一闪,一刀横斩封喉。秦淮咬牙,内力贯掌,硬接刀势,身形被震退数丈。两人一前一后夹击,秦淮被彻底牵制。几息之间,便已气息紊乱。他知道,这一战若再如此缠斗,恐怕命也得交代在这条破巷中。他眸光一沉,手中动作忽变,暗纹手套“嘶”地一声爆出金光,掌心涌出一缕缕细如发丝的毒丝,在空中激射成网,寒气扑面,隐隐带有一股灼喉腐骨的剧毒。柳夭夭轻呼一声,剑尖一荡,腾身避开。陆青目光一凝,足尖一点,强行横身旋退。毒气将两人迫退数丈,秦淮终于得了一息之机。他剧烈喘息,眼中杀意犹存,唇角却露出一丝狞笑。——后援,到了。巷尾街角,一声沉重的锣声从街心传来。如同打破沉默的低钟。数十道黑影自街口、屋檐、坊门两侧同时跃出。黑衣、黑面、青纹、劲装。搅月楼,现身!那是一支完全听命于秦淮的死士部队,悄无声息,却行止如军,齐齐将陆青、柳夭夭与后方赶来的影杀队拦在街前。巷口一瞬间沸腾,杀声起处,寒光交击,战局爆发。而秦淮站在乱流之间,像是终于喘过这口气,他抬手拭去唇角血丝,眼神重新变得平静。他吐出一句话:“不过尔尔,一切……尽在算计。”秦淮脚步虚浮,衣袍微荡,目光依旧冷厉,左手死死攥着那枚锦盒,右袖中微不可查地捏着一粒药丸。就在搅月楼的杀士欲从暗巷逼出,准备接他离去之时。远处,一道孤影踏入战圈,他听见街口一阵轻巧脚步,像是从茶铺中走出来的人,慢悠悠地踩在街心的青石砖上。他不快不慢,一步一摇,像是刚刚买完酒菜,要回家晚饭的市井闲人。朱晏。还是那身破褂子,还是那双布鞋,手里还提着一根沾了糖的竹签,像刚从城东的糖画摊子回来。可是他脚步踏入街心的那一刻——整个街巷,像被无形之手按下“静止”。杀声仍在,但仿佛变成背景的模糊轰鸣。寒光交错,却再无一人分心旁顾。所有目光,都落在了他那副吊儿郎当的身影上。秦淮的眼神顿时一凛,身体微不可察地紧绷。“……怎么是他?”他喃喃。朱晏叼着糖签,看似随意地走到街中央,站在两方阵线之间。他没说话,也没亮武器。但他的到来——就足够让秦淮明白了。夜巡司,不再是他的盟友。不是旁观者,也不是静默的棋子。那是站在刀背后的,推手。而这一刀——就等着他什么时候“自己”撞上来。朱晏像是完全不知此处刚才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,只打量了一眼满地横尸与残破墙檐,叹了口气:“啧,浮影斋这一带,生意怕是要歇几日了。”秦淮眼角抽搐,嗓音略哑:“朱晏……你来的可巧。”“巧?”朱晏挑了挑眉,拎着酒壶轻晃了晃,“是你把浮影斋的酒说好喝,我这不是应邀来尝。”“那你来的……是替夜巡司传话的?”秦淮语气略带期待,却更像试探,“今日之事,是否……还有缓和余地?”朱晏歪着脑袋笑了笑:“你问我是不是代表夜巡司,那得看你信不信我说的。”“我不信你。”秦淮声音沉了下来,“但我信夜巡司。只要你们肯开口,我未必不能退一步。”“退?”朱晏像是听见什么笑话,扬眉笑道:“你是说,从这儿退到搅月楼?还是再退回东都内城,退到朝堂之上?”秦淮怒气压不住了,寒声质问:“你们夜巡司便是这般背信弃义?你们当真要与我撕破脸皮?”朱晏却还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,手中酒壶晃了晃:“这话说得好生怪。你秦阁主当年在南街一手挑起三宗械斗,又在云陵暗杀镇北王使者的时候,可曾问过谁‘信义’二字?这年头,信义这种事啊,哪值几个钱?”“你!”秦淮额角青筋暴起,一字一顿,“你这是代表夜巡司封我去路?”朱晏耸耸肩,笑意缓缓敛去,只吐出四个字:“此路不通。”秦淮眯了眯眼,像是要再说什么——忽然,一阵地动山摇般的声响自街道尽头炸起,震得墙檐尘灰扑簌而落。一声怒吼紧随而至,如山中猛兽啸动,铁与铁的回响震彻夜空。“呔——!给我躲开!!”一柄沉铁巨锤破空而至!封猛来了。那铁锤百余斤,丈长锤柄缠以红绫,如流星坠地,带着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砸向秦淮。锤尚未到,人未及前,气已先至,连搅月楼的杀士都本能地往两旁避让,脸色骤变。“找死!”秦淮怒吼,右臂一甩,暗纹手套如蛇翻腾,真气暴涨,以毕生功力硬生生接住巨锤一角,斜引之势,将其牵引偏向!“轰!”锤头砸中街边的一座茶肆,砖石飞溅,木梁炸裂,整间茶铺垮塌下去,尘土漫天,震得街道两侧的人群连连惊叫。秦淮借此卸力,但双膝微屈,额上冷汗涔涔,口中一甜,几乎喷血。他强提一口气,咬牙低吼:“不过如此!”就在此时,他身后杀士呼啸而至,齐声道:“阁主,撤!”他眼中掠过一丝劫后余生的庆幸,正要喝令离开——街边,那被巨锤砸塌的一线残墙下,忽然一道暗影闪现。不是封猛。我,立于断瓦残砖之后,身形半隐于烟尘与残垣之中,气息如枯木寒泉。早在封猛启动之时,我已隐于他身后多时,并随着人与锤的遮掩不动声色。“……终于,等到你气竭。”我轻声喃喃,眼中悲意如潮水倒灌,七情之力·哀,自心底喷涌而出,刹那间蔓延四肢百骸,化作我一击之间最沉的一刃。我冲出砖垣,悄无声息掠至秦淮身侧。那一刻,天地如静止。秦淮刚刚转头,眼中尚带惊诧。我已出手。七情之一·哀,化为一线幽光,秦淮原想以双掌做最后的阻挡,怎奈刚才那一击已使他气血上涌,根本无法提气,这一剑,贯穿他胸腹之间,鲜血在一瞬间盛放于空中,如同一朵开在寒夜中的血莲。“你……”秦淮喉头溢血,眼神中是难以置信的挣扎。我贴近他耳边,低声吐出一句:“你失算了。”他脚步虚晃,身躯摇曳,终于再无力支持,仰倒在街心青石之上。血染了他那双精致的暗纹手套,染红了他苦心经营的东都棋盘,也染透了,他最后的算计。我缓步上前,踩过乱砖血迹,来到街心。夜色未退,街巷重归沉寂,连先前战斗的余波仿佛都被夜风抹去,只余地上斑驳的血迹,像是刚刚绽放又被风卷残花的梅红。朱晏倚在街口的石灯下,神情懒散,像方才只是路过买酱油的邻居。他垂着眼皮,望着脚下随风飘起的一片布角,没有抬头,只语气淡淡地道:“你想要的,已经大抵如愿。”我走近一步,低声:“朱兄,此番多谢。”朱晏斜眼看了我一眼,唇角扬起似笑非笑:“景公子,别谢得太早。这东都的局才刚动一子,你既已入场,就得演到底。”他顿了顿,又似是随口道:“你想谋一席之地,就该守住那份局中人的身份,别回头,别心软,也别手软。”我目光微沉,缓缓点头:“我知道。”远处传来几声短促的呼哨,是夜巡司在清扫残局,街巷之间残影飞掠,那些搅月楼的杀士尚未逃出三个巷口,便被夜巡司与影杀联手截断。数十柄冷刃在夜色中划出轨迹,仿佛一张织密的天网缓缓合拢。几声低哼和痛叫后,东都的南街,终于真正归于死寂。我转身,走到街心,原先秦淮倒下之处。只见一滩血迹蜿蜒伸展,未干,在冷风中缓缓凝固。旁边,是那枚锦盒,木制外皮沾满灰尘,静静躺着。可——人呢?我微一怔,沉下身,指尖掠过血迹,那温度已微凉,确是溅出不久的血。可四下望去,连一丝拖痕都无。秦淮的尸体,仿佛被风带走。这不可能。除非……他从未真正死去。“他人呢?”
是陆青的声音,带着低沉的怒意。他自左巷跃下,衣袂尚带血色,一双眼冷若寒冰。紧随其后,柳夭夭也翻身落地,拍拍手上的尘土,皱着眉看了一圈:“我刚绕后时,明明看到你那一剑刺穿了他……怎么现在什么都不剩了?”我没有立刻回答,只沉默望着那滩血。那不是假的。那剑,也不是刺偏了。可现在——我轻声道:“他若真能在气竭之下还逃出生天,那今日……只是逼出他的一张牌。”陆青沉声道:“不除此人,东都无宁日。”我点头,低头捡起锦盒,指腹摩挲着那道微微凹陷的刃痕,缓缓闭眼。“此局暂成,可人未除。我们只能——”“从长计议。”夜色如幕,灯火未明。而那摊血之下,仿佛藏着的是一个未竟的杀局,以及更深的迷雾。夜已深,浮影斋后堂的灯火昏暗,一盏青瓷灯静静燃着,油焰轻颤,映出墙上一道模糊的影子。我独坐在屋中,未着外袍,茶未温,窗未关,整个人如失了魂。指节微颤,掌心尚残着那一剑穿透 flesh 与命门时的余震。我的手……还在抖。案前那只盏,参半苦茶,参半血味。手指紧握,却无论如何都止不住颤抖。那一剑,我是如何藏身于封猛锤后的墙影,又是如何借风声与瓦破之机,跃出身形,趁秦淮旧力已竭、新力未生,一剑封喉——我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可他还是走了。不,准确地说,是我杀不了他。不论是心软,还是命数。我抬头,望向那扇未掩的窗,风吹动竹帘,带起几缕纸屑般的寂寥。我到底……错在了哪?我不是第一次杀人。但这一次不同。我精心布局、百般算计,挑起夜巡司与秦淮的矛盾,又拉拢陆青、柳夭夭与影杀,甚至以一份伪密函引他入局——可到最后,我却像一个在泥沼中挣扎太久的人,终于爬上岸,却抬头发现自己站在了另一处更深的淤泥前。江湖的规矩,是生是死,看的是心狠手辣。可我是个大夫啊。归雁镇时,我救过乞儿、官兵、甚至救过来刺杀我的人。可现在呢?我以一大锤为幌,以街头杀局收网,只为逼他信我、走我设好的路,然后一剑封喉。“我到底,会走向哪里?”我喃喃自语,声音低得仿佛一丝灰尘。忽听门外脚步轻响,推门入内的,是林婉。她未着华服,只着一袭青布常裙,手中捧着一盏参茶,轻声道:“君郎,夜深了,该歇歇了。”我望着她,眼中莫名有些湿意,却笑不出。林婉放下茶盏,看了我片刻,没有问,也没有多话,只是轻轻坐在我身边。她伸出手,触到我还在颤抖的掌指,眉头一皱,却并未急着责备,而是轻柔地包住了它,像小时候替人暖伤那般,一点点揉、捂、安抚。我低声道:“我算计了一切,唯独没算到……秦淮能在那种局势下脱身。”林婉:“他老谋深算,一生都在破局中生存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”我摇头,苦笑:“可婉儿……我今日在街心那一剑,虽有大义为名,却终究是暗算。”“我骗了他,设计他,图的是他的命。”“我这样的人……真的还有资格,说自己是个大夫吗?”林婉静静地听着,待我说完,才轻声道:“你是大夫,景曜。可大夫并不是不沾血就能救人。”“有时候,要救的是一个人;有时候,是一城、一国,甚至是你自己。”她眼神澄澈,如夜色中唯一亮着的灯火:“你所做的每一件事,都没有忘了初衷。你没有杀错人,你只是做了那个没有人敢做的选择。”我心头微震,望着她,忍不住喃喃:“可若我从此走下去,是不是就真的……再也回不去了?”林婉微笑,将自己送入我的怀中,轻声道:“若你终有一天真的忘了底线,真的不再痛苦,不再挣扎,不再犹豫——那才是你真正堕落的那一刻。”“可你不是。”“你还会问,你还会悔。那你就还是你。”我怔怔地望着她,仿佛忽然明白了什么,胸腔一阵酸楚翻涌,再也说不出话来。我伸出双臂,缓缓将她抱入怀中。林婉身子一颤,却未挣开,只是轻轻靠在我胸前,低语:“没关系,累了就靠着我歇一歇。只要你不放弃我,我就永远不会放开你。”
风,从窗缝中吹入,带起灯火轻摇。浮影斋后院·屋檐之上夜色浓重,东都已入子时。屋瓦上积水未干,风过处,轻轻泛着涟漪。柳夭夭单膝半蹲,望着景曜所在的屋子,指间转着一枚细细的骨针,眸光却深不见底。“你倒是狠得下心。”她轻声嘟哝,语气却无怒无怨,反倒带着一点古怪的心疼,“那人若真死透了也好,可惜……又是空局。”她看了眼远处陆青守望的院角,那人已倚柱沉思,周身刀意依旧未散,冷得像孤岭霜锋。柳夭夭挑挑眉,收回目光。她知景曜此刻的心情,太明白了。从他用调动陆青的那刻开始,从“封猛”锤下前那抹如烟之影闪出,她就知道——景曜,是用尽了所有筹码来赌。她突然笑了一声,很轻,却带着点像是宠溺的无奈:“你若真狠得下心,也不会一直手抖吧,大夫哥哥。”她忽然躺倒在瓦面,望着夜空那颗孤星,心道:“也罢,你在泥里翻,我在天上看,等你厌了风雪,下来喝酒就是。”浮影斋后屋·窗影之外沈云霁手执香灯,静静地立在屋外几步之外。风穿过朱纱灯笼,在她衣袖上投下一圈又一圈动摇不定的红光。她没有走近,也没有离去,只是远远地望着那一扇虚掩着的门。门内,是景曜与林婉。她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,但她知道那里面的气息很温柔,是她不该也不愿破坏的温柔。良久,她才低声自语:“你终于……动手了。”她语气中没有责怪,也没有惊讶,只是淡淡的忧伤与自我疏离。“你说过,杀人不是你的事……可你终究杀了人。”她的声音轻得像一抹雾,“你是大夫,不该沾血,可你却甘愿染指这局,为天下……也为我们。”她看着屋中那盏不灭的灯火,心底忽然浮起一个模糊的念头:“若有一日你真的杀红了眼,走上那条再也回不来的路……那我,会不会也只能像现在一样,只能远远地看着?”灯影流转,她的身影缓缓隐入夜色,仿佛她从未出现过一般。东都·靖庙后·夜巡司内堂冷香袅袅,墙上挂着一道未干的山水图,墨色未尽,锋意未藏。朱晏立于堂中,仍是那副吊儿郎当的打扮,袖口还有血迹未净,但整个人却比往日寡言许多。案后,司马先生拈起一枚铜筹,在指尖来回打转。青光一圈一圈落在他眉间,像他那从未明说的权衡。良久,他轻声道:“说说吧,从你们见面开始。”朱晏不急不缓,细细陈述从浮影斋设局,直至封猛掷锤、景曜现身、秦淮倒地,一字未漏,语气不动。司马先生听罢,未即回应,只将那枚铜筹轻轻放回盒中,随手取过身边文案,摊开,是一幅完整的东都街区图。他取笔,于浮影斋前做了一个红圈,继而向西,点出青石街、搅月楼、墨屏巷尾三处,最后笔锋一顿。“你说,最后只余一滩血,秦淮的尸身却不见?”“不错。”朱晏神色平静,“我与景曜都以为他已经是穷途末路,哪知仍被他留了一手。”司马先生没有出声,只是在图上勾出一个细细的箭头,自墨屏巷折向城西偏门。“他不会回搅月楼。”他说。朱晏眉一挑:“不回?”“搅月楼虽是他的基业,但今夜搅月楼众全数暴露,已被我们记录在册。”司马先生淡淡道,“那不是他的归宿,而是他给他人看的‘根’。”他敛目凝思,道出一句:“真根……在‘他人不知’之处。”朱晏点了点头,似有所悟:“阁中传闻,他在城西设有一‘镜阁’,可供秘会与藏身。只是无人能证,皆当传言。”司马先生将手中笔放下,转向案侧的另一份简册,上书:“局后善后·景曜卷”。他翻开第一页,目光落在“浮影斋局势总览”上,缓缓开口:“此战,景曜之局几可谓缜密——以情动夜巡司,以局引秦淮,以奇取破局。”“其人虽未正面杀敌,却以‘哀’之力伏于千算之后,终得一击必杀。”“此等心术与心志,实非常人。”朱晏轻笑:“我那时见他手在抖——心志虽沉,终究未脱初心。”“他未脱初心,是好事。”司马先生却冷笑,“可这世道从不会奖赏初心之人。”他合上卷册,目光投向夜窗之外,东都高墙内灯火星点,犹似昨夜余火未熄。“秦淮未死,便不会善罢甘休。他若遁形,必反扑;而景曜,已无退路。”“夜巡司该怎么办?”朱晏问。司马先生缓缓起身,声音仍温和:“我们,是秩序的手,不是乱世的刀。”“秦淮尚未显明反心,不能由我们动手。但我们……也绝不会再替他遮掩。”他负手缓步,走至竹帘前,淡然道:“命人盯死城西、城南、青楼、旧码头……尤其是‘镜阁’传闻地段。”“若三日内无动静——传我令。”“秦淮为不臣者,夜巡司将不再庇护。”“而景曜……”他顿了顿,“可暗中观察,列入候举之人。”“此人,未必不能为我所用。”朱晏耸耸肩:“你倒是也下注了。”“下注?”司马先生微笑,“东都本就是个大赌局。”“这次,我赌景曜。”(未完待续)
喜欢Cslo朋友的这个帖子的话,👍 请点这里投票,"赞" 助支持!
帖子内容是网友自行贴上分享,如果您认为其中内容违规或者侵犯了您的权益,请与我们联系,我们核实后会第一时间删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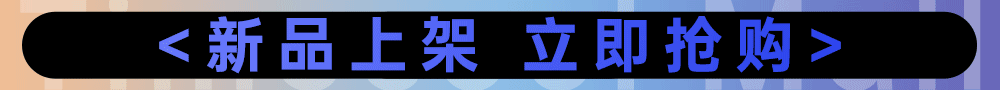
打开微信,扫一扫[Scan QR Code]
进入内容页点击屏幕右上分享按钮
楼主本月热帖推荐:
- 【待李子成熟时】(33-34) 作者:JJandG 2025-04-02
- 【柔情肆水】外传 鞭笞的艺术 (完) 作者:坚持不懈A 2025-04-02
- 【媚肉守护者】(239 完)作者:七分醉 2025-04-02
- 【丈母娘来访】 (11 完) 作者:Archibald 2025-04-02
- 【恶贯满淫】(1-2) 作者:Archibald 2025-04-02
- 【神御之权(清茗学院重制版)】(520)作者:keyprca 2025-04-02
- 【关于我重生之后,终于让女友成了骚货这件事】(9) 作者:嗒嗒 2025-04-02
- 【我这系统不正经】(9.18-9.19) 作者:棺材里的笑声 2025-04-02
- 【私家女侦探】(1) 作者:筱筱 2025-04-02
- 【穿越废土世界却觉醒了18禁系统】(66)作者;冰糖大橙子 2025-04-02
- 【我的陪读丝袜美母】(38) 作者:卡农变奏 2025-04-02
- 【艾泽邦尼亚传奇第一季:铅色森林】 (16) 作者:骨折的海绵体 2025-04-02
>>>查看更多帖主社区动态...